河北死刑循环之原伟东的冤魂作者李宇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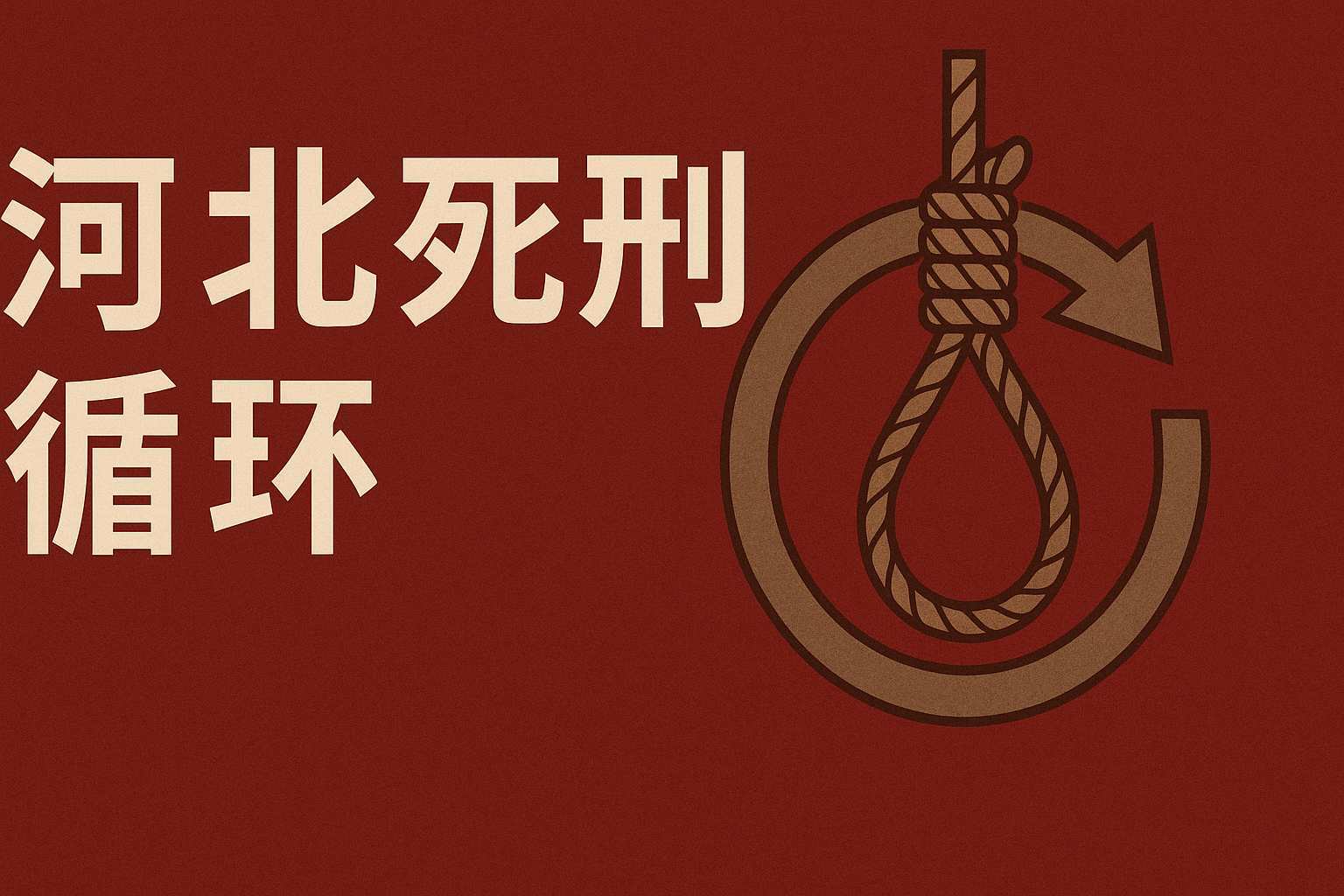
河北,廊坊。1995年11月29日。夜。
空气冰冷,刀子一样刮过胜芳镇的每一条巷子。
一间民房。门轴发出微弱的呻吟,随即是沉闷的撞击声,压过了风声。
杨长林家:
血腥味,很快和着尘土渗进冰冷的房间地面。
《现场勘验笔录》冰冷地记录:
洋镐。菜刀。尼龙绳。一块黄色日产石英手表,指针停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时刻。
三具尸体,杨长林及其两个儿子。
一个幸存者,杨长林的妻子张金萍。
她最初的陈述,像被击碎的玻璃,模糊不清:“进院门,就被打晕了。”
六年。时间像砂纸,打磨着记忆,也可能重塑。
警方的车再次停在她家门口,带走了她。
新的笔录。新的说辞:“装死,眯着眼,看见了。”
看见了什么?谁?
案子,像一块寒冰,沉在那里。
2000年12月22日。胜芳镇。依然是冬天。
刘德成一家三口。又一个灭门。
恐惧像病毒一样在镇上蔓延。
原伟东的早餐店开在刘家对门。
他成了目标,一个标记出现在警方的地图上:
十年后,河北高院会承认,这是一场错案。六人被判无罪。
但那是十年后。在此之前,四个名字,已经和死刑判决捆绑在一起。
原伟东的声音,在最初的喧嚣中几乎听不见:“农业税票。通话记录。能证明我不在。没人去查。”
那张薄薄的税票,字迹清晰:案发当日,原伟东,远在东北。
它静静躺着,像一个被遗忘的证据。
调查。警方的逻辑链条,像一条绞索,开始收紧。
原伟东,不仅是刘德成案的凶手,还被迅速追认为五年前杨长林案的元凶。
旧案的物证呢?那块手表,那把洋镐?
办案机关。一纸说明,轻飘飘地落在卷宗上:
1995年卷宗,所有关键物证,均已丢失。
理由?因为警方搬了家。
案件的齿轮,开始疯狂倒转,碾向原伟东。
2001年。东北。原伟东的家。
门被撞开。没有敲门声。
他从被窝里被拽出来。冰冷的铁器扣上手腕,然后是脚踝。
刑警杜国利。眼神锐利,嘴角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弧度。他没多说,一支枪管顶住了原伟东的头。
没有法律文书。没有解释。
河北的风,从敞开的门灌进来,硬得像铁。
审讯室。灯光惨白。
杜国利坐在对面:
“编。”他开口,声音不大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:
你得给我编出个故事来。
原伟东说自己当时在东北,不可能在河北杀人。
“不编?不说实话?”杜国利笑了,笑意不达眼底。“收拾他!”
角落里,电棍的指示灯幽幽一闪。
一部旧式摇把电话机被推到桌前。几根磨损的电线,末端裸露着铜芯,在灯下闪着寒光:
高科技测谎仪。
杜国利说。
电话线,缠上原伟东的脚趾。摇把开始转动。
咔哒,咔哒,咔哒。
电流的刺痛,从脚底直冲头顶。身体不由自主地痉挛。
杜国利的声音,在电流的滋滋声中,清晰可辨:“打着你说,也得说。”
李杰。原伟东的妻子。同一座看守所。不同的审讯室。
她面对杜国利,眼神坚定:
案发那天,他在哈尔滨老家大队交农业税。他不可能杀人。
她要求调取税票,通话记录。
杜国利没有理会。一张拘留证拍在她面前:“包庇罪。”
如果。如果那时有人去镇政府。但没有如果。
老虎凳。冰冷的铁条压住四肢。
电棍。电话线。
警察轮番上阵。问题千奇百怪:
天上的星星有几颗?不许说不知道!
答不上。电击。
杜国利的声音,像梦魇:“我们提上裤子扫黄,脱了裤子嫖娼。”
他看着李杰因痛苦而扭曲的脸:“脚上的电话厉害,还是手上的电话厉害?”
她咬断了自己的头发,嘴唇肿得粘在一起,满是血沫。
电流穿过身体。有人形容那种感觉:
像肠子被一点点拽出来。
李杰晕厥。冷水泼醒。
她用牙齿死死咬住衣领,试图抵抗。换来的是更猛烈的电击。
杜国利把电棍杵向她的嘴:“今天你要是交代不了,就把你丈夫弄过来。让他看着你受刑。”
18天。老虎凳。双手反铐。
例假来了。没有卫生巾。
一个男警察,跟着她进厕所,扔给她一张揉皱的旧报纸。
“这就是你该用的东西。”他说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李杰的头,一次次撞向冰冷的暖气片。血,溅在墙上。
杜国利看着她,语气带着嘲讽:
你刚从战场回来啊,烈士!
这些“手段”,杜国利们运用娴熟:电击生殖器、开水烫伤、牙签扎指甲缝。
尊严,连同证据的可信度,一同被碾碎。
2001年。指认。
幸存者张金萍被带到一个房间。
四个男人站在对面。
只有一个,戴着手铐,戴着脚镣,剃着光头。
她伸出手,指向他。
指认完成。
原伟东。
2002年。廊坊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,又一份说明:
1995年现场提取的菜刀、钢镐,以及残缺掌纹样本,均因装修、搬迁,证据遗失。
2014年。警方再次出具说明:
犯罪现场原始卷宗丢失。
落款单位,霸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,只用一句“已出具过说明”轻描淡写地带过。
“程序合法,无刑讯逼供。”这是霸州公安局2002年出具的证明。
原伟东的入所体检记录,却像一道刺眼的伤疤:舌头被电伤,耳朵有外伤,腿部肿胀。
同案被告人汤凤武的体检报告,同样记录着全身的伤痕。
多年后,杜国利的名字,会和“刑讯逼供”、“国家发证的黑社会”这些词联系在一起。但在当时以及如今的官方宣传里,他是一线的破案英雄。
刘赐喆。与原伟东等人同时被捕的另案嫌疑人。
他没能走出审讯室:
死因,电击。
2002年。两起灭门案,七名嫌疑人。同庭受审。
被告席上,他们纷纷翻供。
每个人都要求当庭验伤。
法官的目光,在案卷和检察官递上来的“刑讯逼供不存在”的说明之间游移。
没有录像。没有原始物证。没有验伤结果。
只有办案警察自己签署的承诺书。
法槌落下,声音沉闷:
不要再讨论刑讯了。讲案情。
从那一刻起,案件的轨道,被牢牢固定。
“卷宗丢失,可以补充一份说明。”公诉人平静地陈述。
法庭内,一片压抑的沉默。
原伟东,以及其他几名被告人,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数字游戏:
五次被判处死刑,三次上诉,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“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”撤销判决,发回重审。
每一次发回,都像把人从深渊边缘拉回一点,然后再次推下。
2009年,河北高院的合议庭结论:全案事实不清。
然而,改判:原伟东、汤凤武死缓。物证,依然是“找不到”。
真相,和那些丢失的物证一起,被深埋。
2013年。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。案件回到廊坊中院。这是第四次重审的开始。
最高法明确指出:
非法取得的证据,必须排除。
然而,廊坊中院,在排除了那些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后,以更加不足的证据,再次判处原伟东死缓。
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质问公诉人:“你们连案发现场的直接证据都没有,怎么能证明他是凶手?”
公诉人沉默片刻,回答:“案件主要依赖于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。”
原伟东的声音沙哑而无力:“那些供述,是在生不如死的酷刑下编造的。”
而那位关键的幸存者张金萍,在一次关键作证前,突然被警方带走几天,回来后指认原伟东时,原伟东是唯一戴着手铐脚镣的人。
2002年的勘验笔录中,清晰记录着案发现场提取的大量物证:茶缸、恐吓信、残缺的掌纹,还有血迹。
所有这些物证,连同原伟东的生物信息样本,进行比对。
结果:
均未比对出一致结果。
换句话说,没有一份直接物证,能将原伟东与那两起血案联系起来。
办案机关为何依然坚持?
法庭上,没有答案。
河北廊坊,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刑警杜国利的那句话,被律师当庭念出,像幽灵一样回荡在法庭:
这个案子是你做的也是你做的,不是你做的也得是你做的,冤也要把你冤死。
杜国利,这位自称“国家发证的黑社会”,依然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破案任务。
2023年6月。河北高院再审。
这场审判,是原伟东用胃癌晚期的生命换来的。
开庭的日子,廊坊中院外,风声萧瑟。
“我一定要到庭,为了无罪的希望,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”这是原伟东在开庭前的最后一句话。
然而,当天早上,法庭的决定,像一盆冰水:让辩护律师到一个小房间商量——劝原伟东放弃出庭。
律师回到休息室,征求原伟东及家属意见。结果是预料之中的:不同意视频开庭。
但合议庭的决定,比冰水更冷酷:对原伟东中止审理。对同案的汤凤武,继续开庭。
原伟东的姐姐情绪激动,被几个法警强行抬走。旁观者形容:
就像杀猪一样。
汤凤武,被六七个法警从候审室拖到法庭,用拘束绳紧紧绑在椅子上。手铐和脚镣在灯光下格外刺眼。
旁听席的信号突然中断。一片黑暗和沉默。
法官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:“他不配合庭审。”
汤凤武嘶哑的哭诉声穿透出来:“我被刑讯逼供!塑料袋抹芥末油套头,喝辣椒水,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!”
他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,却没有激起一丝涟漪。
当年警察对他说过的话,又一次浮现:“小武子,是你也是你,不是你也是你,冤也要把你冤死。”
法警和法官走到他面前,低声劝他冷静,“有话开庭时说。”
于是,庭审继续。
公诉人在举证时,唯一可以播放的“物证”,是幸存者张金萍当年的辨认录像。
辩护律师当即要求当庭播放。
法官拒绝了:
录像问题以后再解决。
几位法官三次低声商议,结果不变:拒绝播放。甚至一度中止庭审。
那段关键的录像,始终未能在法庭上公开。
律师申请公诉人和合议庭成员回避,被当庭驳回。
汤凤武彻底爆发:“法庭上连证据都不出示,你直接枪毙我就得了!”
他当庭解聘了辩护律师。
他的愤怒,定格在那个瞬间。
法庭外,几十名律师、媒体记者和家属聚集,等待旁听。法庭内,法官宣布不允许原伟东本人出庭,只能通过视频方式出席。
律师提出要求庭审直播,让全国人民见证,被当场拒绝。
原伟东的胃癌已经发展到晚期,肿瘤疯长至11厘米。
他唯一的请求是,先宣判他无罪,再让他接受治疗。
然而,漫长的拖延与失控的审判程序,像一把无形的钝刀,将他的生命一点一点割裂。
“1995年的卷宗和物证丢失得干干净净。”这是二十多年来,唯一清晰的事实。
庭后,原伟东的辩护律师王兴面对镜头,声音疲惫却坚定:
如果没有物证,仅凭言辞就能定罪,那法律的底线究竟在哪里?
2024年6月。河北高院第五次二审开庭。
多年前的一次庭前会议纪要中,河北高院的工作重点赫然写着:庭审安全稳控。
合议庭的内部笔录,白纸黑字:全案事实不清。
然而,最终的结果却是:维持原判。
“我没有杀人动机,没有杀人目的,我为什么会被判了五次死刑?”
这是原伟东在庭上的疑问,也是所有关注此案的人心中无法释怀的死结。
出庭的检察员在法庭上当庭表态:“我们将在庭后就此案提交法律监督意见,要向法院提出意见。”
他们对辩护方提交的一份录音证据(原伟东姐姐与一位关键人物的通话内容)的程序感到不满。
检方的理由是,旁听人员不能作为证人提供证据。
辩护律师指出,这段通话发生在庭审之前,逻辑上与旁听身份无关,更重要的是,通话内容的核心并非原伟东姐姐的陈述,而是电话另一端那位关键人物所说的话。录音不过是作为视听资料呈现的一种证据形式。
“物证丢了,案卷丢了,辨认记录和生物比对信息,你说丢了就丢了。”
这是法庭记录中,让人感到荒诞和无力的一部分。
一位证人在下午出庭,他带来了一个新的细节。他说,公安当年曾向他展示过一幅彩色画像。
这与案卷中仅存的那幅黑白画像完全不同。
证人断言,当年现场曾有多幅画像被制作和展示,而卷宗里仅存的一幅,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。
他的话语,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。
法庭上,辩护律师质问:公安机关是否隐匿了关键证据?是否故意遗漏了不利于指控的材料?
另一位当年的嫌犯作为证人回忆起自己的经历。他被公安抓捕后,不断遭受刑讯逼供。电击、殴打、威胁,让他在无边的恐惧中放弃了所有的辩解:
杀人的事我没有干,抢劫的事,我不得不认了。
他说,当年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离开那个看守所。哪怕是认下一个十年的抢劫罪名,他也不敢再提起上诉。
这种绝望的妥协,在法庭上被还原,证人对刑讯逼供的细节描述,让现场的气氛更加压抑。
原伟东的辩护律师语气克制,但字字千钧,他们指出,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必须传唤廊坊市霸州公安局的所有办案人员,他们需要对案件中大量丢失的案卷、矛盾的证据链以及可能被隐匿的关键材料做出解释。
他直言,这起案件如果不能得到彻底的公正审理,将是河北司法的一次历史性错误。
然而,法庭另一侧的检察官们,只是面无表情地翻着手中的卷宗,没有任何回应。
有律师分析,那些关键的卷宗可能并没有真正丢失,而是被侦查机关“选择性隐匿”了。
他指出,这些卷宗被特意隐藏,目的在于掩盖案件侦办过程中的严重失职和程序违法。
然而,面对如此明确的指控,河北省检察院并未做出正面回应,而是拒绝讨论这一问题,理由是:
审判阶段不涉及侦查细节的审查。
另一位辩护律师再次强调,法庭上的任何证据都必须保证来源清晰,程序合法。
然而,检方提供的两份关键的讯问笔录,不仅取证的侦查人员没有出庭说明情况,甚至连被告人原伟东的签名也只出现在笔录的最后一页。
“这些复印件是从哪里来的?”质问在法庭回荡。
2024年。原伟东已被羁押超过22年。
他的双手因当年的电刑而残疾,身上仍留着十多处深色的电击伤痕。
“我没有杀人,”他的声音微弱,“但我知道,我可能很难再走出这个看守所了。”
一份2001年的入所体检表,像一张发黄的罪证,详细记录了原伟东入院时的伤情:“舌头有电伤,腿肿,耳朵有外伤。”
这些伤痕,不仅没有引起任何追责,反而被淹没在合法程序的声明之下。公安局甚至在事后的说明中明确写道:
全体办案人员均系严格依法办案,没有刑讯逼供行为发生。
至于那位发明了“高科技测谎仪”的审讯专家杜国利,早已升任当地网警大队的队长。
死水一般的案件,与被吞噬的命运。
而真相,依然像沉在水底的石头,遥不可及。
2001年到2024年。河北省高级法院,审理此案耗时22年,先后延长审限34次。
每一次家属焦急地询问结果,得到的回复总是那几句:“再等等,稍微再等等,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”
23年的时间里,原伟东经历了六次死刑判决(包括死缓)。
2020年,法院在判决中承认,本案所有的有罪供述均来自刑讯逼供,应依法予以排除。然而,在没有了口供,没有了直接物证的情况下,他依然是杀人犯。
他的姐姐原淑娟,一次次地追问,声音嘶哑:
“没有口供,没有作案动机,甚至连案发现场的物证都丢了,为什么还判他有罪?”
2024年10月17日。原伟东因为胃癌晚期,在医院做了胆管手术。
十天后,他仍然被手铐脚镣固定在病床上。
家属再次递交取保候审的申请,理由简单而残酷:“他随时可能去世。”
法院的答复,依然是那句熟悉的话:“等一等,再等等,会很快的。”
这答复,和二十年前,几乎一模一样。
原伟东的生命,在这样的消磨中,一点点耗尽。真相,却依然远在天边。
8437天。这是原伟东失去自由的其中一天。
在病房的玻璃窗后,他隔着厚厚的玻璃,对着前来探视的姐姐露出了一个极其虚弱的微笑。
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,声音细若游丝:
“姐,我想吃一个苹果。”
原伟东案,不仅仅夺走了他个人的自由和生命,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:
吞噬了他的整个家庭。
母亲金亚芹,为了给儿子喊冤,常年奔波于各级法院,最终在石家庄高院门口磕头喊冤时,力竭而死。父亲原振福,为了查找能证明儿子清白的农业税票,被当地警方以“扰乱办公秩序”为由拘留一个半月,释放后不久,因癌症去世,至死未能见到儿子沉冤昭雪。弟弟原伟刚,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大厅喊冤时,情绪激动,割腕自残,后被以“寻衅滋事罪”判处有期徒刑两年。另一位弟弟原伟明,因为在陪同家人喊冤时,情急之下挣脱了阻拦的法警,被以涉嫌“袭警罪”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。原伟东的儿子,6岁时就被同龄的孩子在背后指指点点,贴上“杀人犯儿子”的标签,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。
“我们一家人,从来没有停止过喊冤。”原淑娟说。
23年过去,原家四散飘零,亲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,案件却依然像一艘在原地打转的鬼船,毫无进展。
他们写下的喊冤信,堆积起来,已有半人多高,却如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
在最后的庭审中,原伟东通过视频,用尽全身力气请求法庭允许他亲自出庭陈述。他说,他不是杀人凶手,他的冤屈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决,他想在法庭上,亲口说出这一切。
那时,他已经身患晚期胃癌,胃部被切除了五分之四,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系统。
河北法院在这23年间作出的一系列判决,像一面破碎的镜子,照见了权力在不受制约时的荒谬与冷酷:
此案不出河北,绝无公正可言。
2024年12月31日,上午9点58分。
河北保定第一中心医院,重症监护室。
仪器的蜂鸣声,变成一条直线。
原伟东,55岁。
他走了。带着未洗的冤屈,和那个未能吃到的苹果的遗憾。
被限制人身自由的8507天,从没有给他留下过一天喘息的机会。
这次住院,从2024年12月21日入院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在病床上的时光被清晰记录。
这9天,他被镇静剂强行拉入昏睡,插管维持着脆弱的生命体征。
就在五天前的12月25日,他还能够与家人进行正常的交流。
从2001年9月16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那天起,到2024年11月2日被送入保定监狱,原伟东的时间被冷酷地划分为三个部分:
看守所7382天,监狱953天,最后是医院里的9天。
一共8507天,二十三年零三个半月,换来了不同法院的10份判决与裁定。
河北廊坊这起跨越世纪的灭门案,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只有系统参与者在场的权力游戏。
参与案件的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,没有谁能,或者说,没有谁愿意站出来为可能的错误负责:
他们用丢失来掩盖证据的缺失,用暴力制造出完美的口供,再用漫长的沉默和程序来消解所有的质疑和反抗。
其中,最高法院指令再审1次,河北高院发回重审的次数是3次,廊坊中院判处死刑的次数是4次(含死缓),河北高院维持原判的次数是2次。
这些冰冷的数字游戏,耗费的不仅仅是纸张、司法资源,而是一个完整的、无法重来的人生。
原伟东死了,河北,终于赢了。
写于2025年5月30日
附:原伟东案法院审理时间线
23年来,原伟东的案子历经10次审理,被判死刑6次。
一、【第1次一审,地点:廊坊中院 结果: 死刑立即执行 】 2003年6月27日, 廊坊中院作出(2002)廊刑初字第112号刑事判决书。
二、【第1次二审,地点: 河北高院 结果: 撤销死刑,发回重审 】 2003年12月4日河北高院作出(2003)冀刑一终字第698号。
三、【第2次一审 地点: 廊坊中院 结果: 死刑立即执行 】 2004年6月2廊坊中院作出(2004)廊刑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。
四、【第2次二审 地点: 河北高院 结果: 撤销死刑,发回重审 】 2006年12月11日,河北高院作出(2004)冀刑一终字第670号刑事判决。
五、【第3次一审 地点: 廊坊中院 结果: 死刑立即执行 】 2008年4月23日,廊坊中院作出(2007)廊刑初字自第11号刑事判决。
六、【第3次二审终审 地点: 河北高院 结果: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】 2009年11月12日,河北高院作出(2008)冀刑四终字第142号刑事判决。
七、【指令再审 地点:最高人民法院结果:指令河北高院再审 】 2013年7月1日 ,最高人民法院作出(2013)刑监字第72号决定书。
八、 【发回重审 地点:河北高院结果: 撤销死刑,发回重审 】 2014年3月24日,河北高院发回廊坊重审。
九、【第4次一审 地点:廊坊中院 结果: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】 2020年7月8日,廊坊中院又判死缓。
十、【第4次二审 地点:河北高院结果:死刑缓期二年执行】2024年10月29日,河北高院维持原判。
十一、【原伟东死了,河北终于赢了】2024年12月31日,原伟东病逝。
特别声明:本文仅代表原作者观点。本网站为转载。

